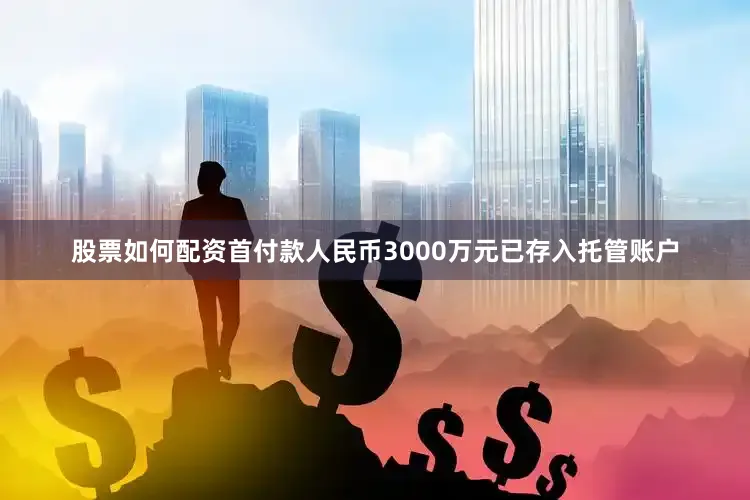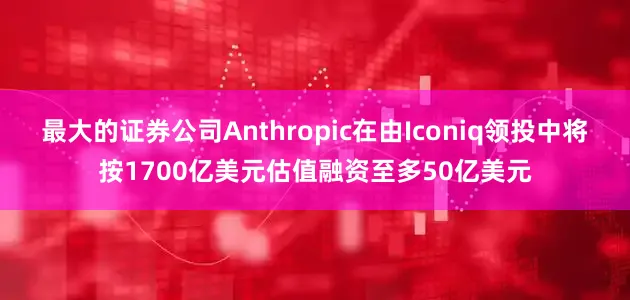一个在新加坡教书的朋友,前阵子跟我讲了个哭笑不得的事。她班里有个祖籍福建的小孩,能把莎士比亚的诗背得滚瓜烂熟,结果写“春节”两个字,提笔就忘。她忍不住问学生干嘛要学中文,那孩子一脸坦然:“我以后进跨国公司,说中文找不到好工作。”
这番话,像根针,一下就扎破了那层温情脉脉的窗户纸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在2023年做了个调查,18到35岁的年轻华人里,只有23%能熟练用中文写东西,超过六成的人觉得,日常根本用不上。

这事儿的根子,得从一百多年前说起。1819年,莱佛士的船一靠岸,新加坡的命运就被钉在了马六甲海峡的十字路口上,成了英国人远东贸易的棋子。经济要转,就得有人。大批福建、广东的劳工涌入,到了1881年,华人已经占了总人口的六成多。但英国人玩的是“分而治之”那套,官场和学校里,英语是绝对的通行证,中文只能在华人自己的圈子里打转。
这种拧巴的模式,让老一辈华人活得挺分裂。一边靠着乡土宗族那套传统文化抱团取暖,一边又得拼命学英语,好在殖民者的体系里混口饭吃。翻开当年的《新加坡华人年报》就能看到,1890年第一所英文学校招生,报名的人挤破了头,比中文私塾火爆多了。有钱的华人商家,宁可花大价钱,也要把孩子送去学英语。

到了李光耀的时代,这种选择变得更加赤裸和决绝。六十年代刚独立的新加坡,就像个刚出生的婴儿,被扔在冷战的寒风里。他在回忆录里写得很直白,必须让西方世界相信,新加坡是“亚洲的西方国家”,不然就是死路一条。为了活下去,就得选边站。
于是,一系列操作开始了。1968年的《就业法》,直接把英文流利度跟政府、外企的饭碗挂钩。七年之后,中文的地位从“官方语言”降到了“第二语言”。这一套组合拳下来,效果立竿见影。到1980年,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飙到9.5%,而当时中国的数字是3.8%。经济腾飞的代价,是整整一代人与中华文化的渐行渐远。当时不是没有华人社团出来呼吁,但声音很快就被“不符合国家发展战略”的大浪给盖过去了。

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。2024年新加坡教育部的课程大纲里,小学英文课时占了快一半,中文只有20%。数学、科学这些主科,更是全英文授课。中文,成了一门需要“额外”去学的语言。所以,也就不难理解《联合早报》去年街采时,八成的年轻人会说,看英文剧、刷英文社交媒体更舒服,只有跟爷爷奶奶说话时,才会蹦出几句夹着方言的中文。
可这世界,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。谁能想到,几十年后,风向又悄悄转了。
一个做外贸的新加坡朋友陈先生感受最深。他说以前跟中国客户谈生意,对方都特客气地主动说英文。现在反过来了,饭局上,好几个新加坡老板开始磕磕巴巴地秀中文,有的还专门请了家教。数据显示,2023年新加坡学中文的人数涨了三成,连带着中文培训班都多开了四分之一。

这背后不是什么文化觉醒,就是最实在的利益。2023年,中国和新加坡的双边贸易额干到了1100亿美元,占了新加坡外贸总额的15%。中国成了新加坡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之一。钱在哪儿,语言的价值就在哪儿。曾经被认为“没用”的中文,突然就成了简历上的加分项。
新加坡教育部也开始“回调”。2022年宣布把中文课时占比从20%提到25%,中学还加了“中华文化选修课”。第二年,又跟中国合办了“中新语言文化交流中心”,一年搞上百场活动。

这种摇摆和拉扯,恰恰是海外华人身份认同最真实的写照。新加坡华人历史学者吴良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:“海外华人就像风筝,不管飞多高,线始终牵在中国。”这话听着有点老套,但历史一次次证明了它的分量。19世纪末中国弱,华人在南洋就得受殖民者的气;九十年代后中国经济起来了,华人在当地的腰杆子也硬了些。
所以,今年春节,新加坡唐人街的年味儿格外浓。红灯笼挂满街,舞龙舞狮的队伍能堵上几条街,很多年轻人甚至开始跟着长辈学着写春联。这种血脉里的东西,是刻在骨子里的,平时可能感觉不到,但一到特定的时节,就会被唤醒。

说到底,文化认同这东西,从来不是靠说教和呼吁得来的。它更像是一种市场行为,一种基于实力的自然吸引。与其去纠结别人到底喜不喜欢你的文化,认不认同你的根,不如把自己的事做好。当一个国家足够强大,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足够好,文化自然会成为一种魅力,而不是一种需要被“拯救”的遗产。

毕竟在这个世界上,实力,才是那张最硬的“名片”。
慧仁策略,股票配资门户导航,配资好评炒股配资门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